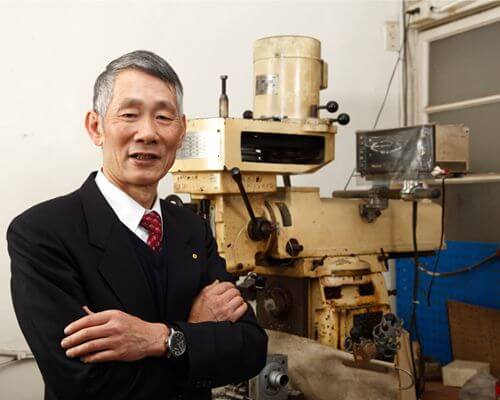「產學合作」這件事很可能已經被玩壞了,本來以為是出路,但這條路上似乎陷阱遍布。
在生技領域「產學合作」某個極為成功的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卻因畢業即失業而焦慮萬分。在精密機械領域也很奇怪,明明多年來有許多產學合作的預算、計畫,現在仍然呈現死氣沉沉,好像不來一針「愛擱發」就會倒光光?
近幾年來,有識者發現學界只重視期刊發表,研究與教學無益產業;業界只重視削價競爭,不重視應用新知識與技術提升價值,並高聲呼籲改革。教育部和經濟部也「從善如流」,推出了許多產學合作計畫,也爭相用採「產學合作」計畫數量、預算數量作為評鑑指標,似乎欣欣向榮,蔚為風氣。但實況並沒有這麼樂觀。
產學合作在台灣,出路已變成陷阱?
某大學的生技研究所以產學合作量極大而備受矚目。但這個實驗室的研究生並沒有因此充滿樂觀,反而愈接近畢業愈憂愁惶恐,為什麼呢?
原因在於,這個大學生技研究的產學合作做得太好,附近許多生技公司都與學校合作進行技術研發。企業出錢,支援部分器材成本、人事費用,大學的教授和研究生就幫企業做研究。由於大學教授已拿大學薪水,而研究生薪資低廉至極,所以許多企業長期產與產學合作,就樂得不必擴充本身的研究部門編制。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諷刺的現象:某些學校產學合作愈成功,教授得到愈多資源和績效,招收到愈多研究生,但這些研究生一旦畢業,就愈可能失業;畢業生離開實驗室之後,正式的研發職缺非常難找。
產學合作打假球葬送掉的台灣前途
「真槍實彈」的產學合作可能反而導致許多失業的研究生畢業即失業,在另一方面,「打假球」的產學合作現象,可能也腐蝕了產學合作的良法美意。
日前訪問到一位業界人士(為了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無法透露姓名),他指出台灣有許多學者、廠商、研究機構互相合作,將教育部和經濟部推動的產學合作視為蹺腳發大財的機會。
這些學者和廠商結盟申請大量補助款項,雙方並沒有真的做什麼研究,只是研究期程到了,業界提供一堆單據把預算報銷,學者指派碩士生將過去既有的研究成悲包裝粉飾一番就可以上交報告,得到的經費各方分食。
品質鬆散和粗劣的研究報告,其實經濟部和教育部都很難審查。到底哪些研究是什麼時候做的,經費是否真的用來研究,成果是否對產業有益,官員的肉眼不可能看出來。就算找學者來當評審,若是隔行就會隔山,同行之間就常常出現互相掩護 — 今天你幫我過關,明天我也閉一隻眼,大家悶聲發大財。這樣的模式在過去審查論文的時候就不曾少過,「整廠輸出」到產學合作的領域,只是使個眼色的工夫而已。
過去幾年,我們終於問對了一件事:學界將力氣投入學術論文,業界不思技術和策略創新,兩者的隔閡是台灣經濟引擎失速原因,怎麼辦?
但我們的答案可能是錯的:編列預算、訂定指標 — 政府各部會用在產學合作投入大量資源,並且列為教授與學校的評鑑要項,至今沒有看到明顯的效益。當產學雙方合作研究,業界卻可以因此不設研究職缺;當產學雙方合作造假,更可以瓜分利益吃乾抹淨,這些現象都無益於台灣長期發展,反而鏟掉、削掉了我們的希望與前途。
本文獲商業周刊網站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商周網站專欄部落格。
出處聯結:商周網站專欄、學與業壯遊(作者網誌)